本文发表于2014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大童缘》(“难忘故事”下辑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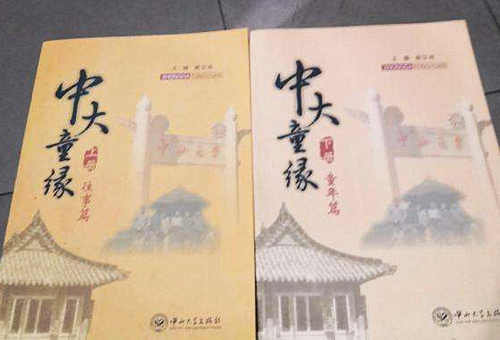
图为2014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大童缘》。(图片来源于网络)

图为刘渠先生一家(后右一为作者刘攸弘)。
坪石,对于每一位曾到过那里的“老中大”,都会有一份难以忘怀的回忆。我仅是一位“老中大”的子弟,对那里同样有着挥之不去的怀想。不是因为那里有一条清澈的武水,自重叠的峻岭中逶迤而至,吹来了南岭的山风;不是因为那里屹立着的金鸡岭,有着太平天国女将洪宣娇在岭上练兵抗击进关清兵的传说;也不是因为那里是岭南通向大北方的一个边陲小镇。我曾数不清多少次与她擦肩而过,却未能看清她的脸庞。真正让我无限怀想的,是那里积淀了很多我小时候的故事,是在那里我生下来就和父辈们一起度过的一段不寻常的日子,更因为那里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“老中大”们同甘共苦于战乱中坚持办学的地方。
1940年,日寇疯狂入侵中国大地,正是全国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阶段。诚然,民族教育不能中断,学校也是抗日战争的阵地。当年8月,中山大学在许崇清校长主持下,又从云南澄江回迁广东坪石,坚持继续办校,并在全国范围聘请教授。我父亲刘渠受聘到了中大法学院社会学系任教。

图为位于坪石的中大法学院办学旧址。(彭剑波/摄)
父亲于1931年在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并留校任教。1933年通过考试,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院公费特选进入文学部深造,选读了人口理论及进行人口问题研究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回国,在梅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,并恢复了在1927年曾秘密参加的中共党组织关系。
那时,战乱一时还没有波及坪石,学校的教学尚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父亲一方面教书,一方面带领学生进行社会调查,详细分析了坪石镇的人口构成状况及进行广东人口方面的研究,相继在《中山大学学报》等刊物上发表了《现代生育率遽降论》、《广东人口研究》、《论人口与职业题》及《小城镇人口构成的分析》等论文,曾当选为第九届中国社会科学社理事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,最大的心愿莫过于能够著书立说。所以在坪石的几年里,生活虽然十分艰难,却是父亲得以充分发挥专业学识的年头。
父亲到坪石后不久,母亲吴梅君也从梅县来到这里一起生活。1941年冬的一天夜里,我即将呱呱落地,镇上的小医院却在河的那边,深夜没有渡船,周围连住户都不多,正不知如何是好。情急之中,父亲赶紧求助于相邻的章导教授夫人前来帮忙,有着助产知识的章伯母终于使母亲得以安全分娩。父母亲跟我一提起在坪石的日子,就会说起这件事,感激之情全家难忘。
最近,徐伯母(徐俊鸣教授的夫人)告诉我,原来在我出生后的第三年,章伯母又为她接生了第三个女儿小英。本来徐伯母自己也是助产师,在坪石曾多次义务为中大家属及乡民接生。据徐伯母的回忆,1943年秋天,我们家因受不了房东老板娘的犀利而退了房子,她正好想从河那边搬到张家湾这边来,就住进了我们原来的房子,几个月后她的小英也在那房子里出生。在那艰苦的岁月里,“老中大”们就像生活在同一条航船上,不分你我,团结互助,一起共渡难关。
60多年后的今天与长辈们说起这些旧事,才知道在那战乱的年代里还有这么巧的事,比我小两岁的小英竟然与我在同一间房子里出生,由同一位章伯母接生。更巧的是,小英后来学的专业又和我一样,都是气象专业。
在坪石的日子,“老中大”互助的例子还有很多,只是那些小事在他们看来实在微不足道而极少提起。然而,大家都有一种融洽、互助、团结的感受,一种永远忘不了的感受,正是这种感受铸成了“老中大”之间的深情。
我所在的家族从爷爷算起,所有叔侄兄弟身高都在1.70米以上,可我特别矮小,还不到1.60米。原来这与我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缺医少药不无关系。母亲说主要是我在两岁时患了“打摆予”疟疾,却买不到治疟疾的特效药“奎宁丸”,身体时好时坏拖了整整一年,影响了长个子。而且,刚出生时母乳又不足,吮奶时吸出的竟然是血,直到出现黑便才发现问题严重,只好未满月就靠吃米糊了。那时候没有米粉卖,还是母亲提着米到农民家里,借用脚踩的舂臼,以非常原始的办法舂米成粉。现在才知道,当时在坪石出生的中大子弟都是靠吃这种粗米糊长大的。
为了增加收入,母亲还要走几里路去中学上课,经常一路难见到几个人,一阵山风吹过芦苇沙沙作响,不禁使人毛骨悚然。母亲说那时最害怕的还不是恶人强盗,而是毒蛇与猛兽,听说山上还有老虎,所以走山路时特别害怕。其实,真的老虎并不易碰上,母亲亦从未见到过老虎,倒是常被毒蛇惊吓。我们住的房子原是房东的柴草等杂物堆放间。有一天,在屋梁上真的就发现缠绕着一条毒蛇,把我们全家人都吓坏了,母亲抱着我赶紧跑到房屋外面,父亲战战兢兢拿着竹竿,只敢远远地把蛇赶走。
根据徐伯母的《世纪的回忆》,也许还是那一条大毒蛇,竟然先后把我们两家人都惊吓过。因为那房子是猪圈改成的,后面有个天井,紧连着一口长满草的小水塘,很适合毒蛇藏匿。一天傍晚,徐伯母突然见到一条眼镜蛇蹿入床底,盘卷在墙角里,竖起三角头吐着蛇信子,十分可怕。还是徐伯母胆子大,不慌不忙地叫当地人来把这条眼镜蛇打死了,之后就再没有毒蛇出现过。
有一次,母亲到镇上买东西,发现站在身边的一个村民偷走了自己的钱包,竟不顾一切地追上去一手把钱包抢回来,并对着村民大声喊“这钱包是我的!”那村民一下子被母亲突如其来的动作惊呆,一时手足无措没有争夺,低着头悻悻地走开。母亲说起这件事就觉得很有意思,这并非是那突然冒出来的勇气,而实在是那时候连小偷都如此朴实。
中大旧址是在老坪石,在武水的西岸较开阔平坦的一边,距离对岸的坪石火车站还有几里路。当太阳从金鸡岭上升起的时候,河面上的倒影十分迷人。小时候,我最高兴的就是到河边看渡船。那时河面较宽,没有桥,靠小船摆渡。父亲很怕吵闹,只要我一闹,就算是下着雨也打着伞抱我出去看船。每到周末,只要没课,父亲还一定会抱着我到渡口去等母亲回来。在坪石的生活虽然很艰辛,但比起山外的战乱已是世外桃源,在那里总算暂时过上了一段安稳的日子。

图为坪石老街(国立中山大学校本部旧址)。

图为坪石武江河畔。(江家敏/摄)
然而,在日寇侵略我国的日子里,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有长久的安定。1945年1月,日寇从湖南宜章及韶关同时进犯坪石,形成南北夹击之势,国民党守军闻风而逃,学校当局通告紧急疏迁。一时间学校师生分头疏散,法学院一批是经曲江、连平再东行赴龙川,最后到达梅县。那时我还不到四岁,逃难时只好请挑夫担着,一端箩筐是我,另一端是书,夹在“走日本鬼”的荒乱人群中。我坐在箩筐里倒是很舒服,挑夫走得飞快,我一定觉得很好玩,全不知大人们沉重的心情。母亲走得慢,人群中转眼间不见了我,这可急坏了母亲,以为我这一回必定走丢啦。恰巧这时碰见了社会系里的几位年轻老师,就请他们赶紧分头追寻。后来,他们总算找到了我一起回到梅县,否则我就是另一家的人或是另一种命运了。抗日战争时期出生的我,尽管是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,却也难逃各种劫难,其他百姓就更不堪回首了。
上面的故事实际上都是“老中大”们讲的,虽然我那时还不懂事,却因为曾有过那些经历,说起来总是感慨良多。现在的坪石早已今非昔比,中大旧址亦无踪影可寻,据说尚存一块写着中山大学旧址的标志。2006年我借公务之机到了坪石,曾打听中大旧址所在,遗憾的是很多当地人都不知其踪,始终未能让我站在出生的原点上作一番追忆。但老一辈讲的这些在坪石的故事将水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如今,坪石的“老中大”多已渐渐远去,据我所知尚健在的还有几位,都是近百岁的耄耋长者。其中徐伯母98岁时仍耳聪目明,还有董伯母(董家遵教授的夫人)及我母亲等,她们不时还通电话叙旧。值此向她们深深地鞠躬,祝尚健在的“老中大”们健康长寿。
(注:部分图片由南粤古驿道网补充。)
(本文由施瑛、阿瑞推荐并提供相关资料,南粤古驿道网综合整理。如涉及版权等问题,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。)
责任编辑:江家敏